#### 前言
第39屆五虎崗文學獎於今年五月落幕,經中文系主任殷善培的查考,肇始於民國67年文理學院時代學務處(之前稱訓導處)和出版中心合辦的徵文活動,而成為常態性的文學獎項則是從民國70年開始,民國82到84年曾因經費不足曾停辦了3屆。歷年來的徵文項目也不是近年固定的新詩、散文、小說三項,而是包括了:極短篇、報導文學、論文等獎項。
這個在淡江持續了39屆的全校性徵文活動,可說是當今文壇的新秀擂台,學生時代的蔡素芬、劉中薇、丁威仁、曹馭博、林念慈都曾經站上這個舞台。正如曾經擔任這個活動多年指導老師的殷善培所言:「寫作是中文系強項,但不是中文系專利,這是全民寫作的時代,我們期待同學在AI浪潮下,能夠也願意藉寫作來澡雪精神,發揮寫作療癒功能,領略人文情懷。」
得獎作品經主辦單位授權,首獎專訪、作品,及評審摘錄於本報刊出,以饗讀者。
#### 【第39屆五虎崗文學獎新詩首獎專訪】
#### 林于勝實驗文體切換 領略新詩減法之美
【記者林育珊專訪】順著耳機線攀藤,構築〈寄生耳機〉的奇幻世界,中文四林于勝透過生活觀察與省思撰寫了〈寄生耳機〉新詩、散文與小說,獲得五虎崗文學獎評審的肯定,榮獲新詩組首獎和小說組推薦獎。林于勝已是五虎崗文學獎的常客,大學期間曾以〈佐德夫的地板〉獲得第36屆小說組佳作,〈智齒日記〉獲得第37屆散文組佳作,〈畢達畢斯先生〉獲得第38屆小說組佳作,持續耕耘於創作,懷抱熱忱,創作出一個又一個角色故事。
「一開始〈寄生耳機〉只是一篇小說」林于勝分享本次作品〈寄生耳機〉創作時的故事,他表示一頓飯的時間有了創作散文和新詩版〈寄生耳機〉的念頭,之所以會有這樣的安排是在和朋友聊天時,蹦出的想法,一開始是朋友正煩惱著該以何種文體投稿這次的文學獎,他就提出三種文體都以相同題目撰寫的想法,只是朋友當下就否定了這想法,表示不想當怪人,但這想法已在他心中徘徊,於是乎三種文體的〈寄生耳機〉分別誕生了。
林于勝分享在三種文體間切換模式給了他許多挑戰也拾獲不少驚喜,他回顧自己的創作旅程和評審的回饋,他表示好像真的能夠感受到「詩是減法」這句話的意義。他表示自己在新詩的創作並沒有太多的理論基礎,就只有高中時以新詩抒發心中情情愛愛的經驗,上了大學後加入文藝研究社就開始鑽研小說的技巧,和社團的朋友相互切磋、一同找尋屬於自己的創作風格,創作的重心放在小說的撰寫上。他這次是首次將同一主題以三種文體來呈現,他回憶創作〈寄生耳機〉時將所有精力都放在了小說上,一直修改直到投稿截止日依然還沒完成心中理想的〈寄生耳機〉,更別說用更多的時間來撰寫散文和新詩,在截止日的半夜時分他才開始著手書寫散文與新詩。他表示由於文體和時間上的限制,他在寫散文時僅以修辭創造真實的懸疑感,捨去撰寫小說時慣用的奇幻筆法,在有限的字數下更是要選擇談及的層面,過程中勢必要對小說進行刪減;他在寫新詩時更是要擺脫撰寫小說時關心細節的慣性,在有限的容量下有意識的刪減,他表示這次投稿時的狀態剛好就是時間很有限,因此他也沒有過多的時間與心力能關注起細節,因此他說:「好像就是因為時間不夠,才能寫好這次的新詩阿!」對於新詩獲得首獎,他心中頗是驚喜,也藉此感受到文體間巧妙的關係。
「我總是好奇路上行人裡的耳機都有著什麼樣的世界?」是這樣的好奇心帶領他找尋與構思〈寄生耳機〉能長成的模樣,他分享〈寄生耳機〉的創作泉源。從行人的耳機到菟絲子的藤蔓再思考自身與耳機的連結,還聽了朋友與耳機間的故事,一番的自我辯論,才創作出科技與身心靈間磨擦出的火花。藉此他也分享大學四年來在創作路上的學習,他表示一群人聚在一起討論小說與創作的經歷給了他許多創作的方向與靈感,回顧四年也能看見自己的成長,從大一時的摸索,大二戀上暗黑、壓抑路線的自我創作,再到大三大四開始關懷與省思社會,試圖用文字傳播心中的愛和念想,每一步的成長都是因為有社員們一起,在校園裡能有這樣的社團讓他收穫滿滿,但他也提及礙於招生困境,這個創作基地也消失了,對此感到惋惜。
最後,他鼓勵並提醒自己和熱愛創作的朋友們,秉持尊重的心,切記創作不是傷害別人的工具,創作是用藝術的手法包裝,持續精進自己,能力讓文字帶著愛到更遠的地方。

第39屆五虎崗文學獎新詩組首獎林于勝。(圖/林于勝提供)
#### 【第39屆五虎崗文學獎新詩首獎作品】寄生耳機/中文研一 林于勝
用Ai生成情慾
愛撫著手機屏幕
用一條鐵線牽起彼此的愛
將你的嬌嗔囚禁於我的耳道
今夜的瀏覽紀錄不會留下痕跡
甘願被你寄生
吃光我的記憶體
讓我們在內存空間狂歡
不停輸入丶輸出
釋放所有壓縮
解剖身體的秘密
放大像素或線條
旋轉丶裁剪丶保存
你的臉龐開始發燙
渴求著充電
我明白視窗關閉以後
你的笑容將會重新啟動
但我還是想將此刻截圖
縱使於往後千百萬次的搜尋
都不會再遇見你
#### 〈寄生耳機〉評審摘錄
*很有趣,他的每一段都達到兩種指涉的精準融合,「機器在發燙」,他說是「臉龐」,字裡行間都很有意思。(顏艾琳)
*題目很吸引人,用一種想像的愛跟這時代新的動作呼應,我覺得蠻新鮮的,能夠給人新的感受。這也是詩的好處,用這種詩的形式,讓讀者感受到一些新的題材魅力。(楊宗翰)
*這首詩極具創意,用了許多網路數位有關的用語,輸入、輸出、壓縮,還有手機要充電等等來隱喻或者說表現情慾的渴求,很不錯。(向陽)
#### 【第39屆五虎崗文學獎散文組首獎專訪】
#### 張嘉恬隨心走筆 在文學世界成為自己的女王
【記者吳沂諠專訪】就讀西文四的張嘉恬,來自台南,表示「嘉」族中有不少喜歡嗜好「恬」食的人。受到家庭氛圍的影響,從中啟發各種靈感,並將親情方面的生活經驗串起來寫入文章中,自己總是在家中扮演察言觀色的角色,發現每位家人之間的相處都有「矛盾點」可以寫,因此將家人間的愛恨情仇鑲嵌成一行行的文句、交織成一篇篇的文章,並加以描述人物的言語、聲調、表情,增添其中的高潮迭起。對心思綿密細膩的張嘉恬而言,寫作已成為抒發心情的絕佳管道。
「『寫作』這件事很奇妙,一開始總是毫無頭緒,但過程卻使我十分投入!」張嘉恬分享,自己從小就養成不斷寫作的習慣,還額外抽空報名作文班,並在國中階段就開始積極投稿文學作品,每當自己進入一所新學校時,都會查詢和寫作相關的比賽項目,自己過去在文藻大學就讀時也曾榮獲文藻文學獎小說第三名、小小說第三名、新詩第二名,以及台積電青年學生文學獎散文組優勝。張嘉恬笑著回憶,過去的自己曾經一廂情願地追求過一段感情,最終卻換來不如意的結果,因此將自我豐沛的情感,在私底下寫了將近七萬字的小說,在文學世界裡她可以成為女王:「我想要讓它怎麼發展就怎麼發展。」
「我喜歡寫平實的生活」她對隱喻、諱澀的文風完全無感,曾經愛上王小苗、顧城、海子等作家的新詩,都是平實又有感,如果文筆有成熟的傾向,肯定是曾經加入文學性社團,潛移默化的緣故。而最近對於「神秘學」的研究,占星、塔羅牌,讓她寫出「拜拜完的食物都會少一個味道,因為靈魂真的來過。」這樣詫異又詭譎的句子來。「我常常作夢。」她的好奇心讓她接納了更多的可能,包括營造神秘氛圍,多一層隱喻,增加延展性,一個伏筆,「好像是一個背書,你講什麼都沒關係,它就是一個夢啊!」〈嗜恬〉的結尾寫到「夢裡的孩子掉了牙」就有神秘學的味道。她說靈感來自小時候聽說傳說,夢見掉牙就是父母要死掉,「四月下雨自己開車去拜拜,想很多事情。」讓她向讀者埋下了伏筆。
升大三那年的暑假轉學來淡江,來到淡江,眼前的山河美景讓她豁然開朗,高高低低,高低差就會不一樣,風景就不同,走一走就餓了。遊歷校園,很開闊很多樹,有很多椅子可以坐下來,坐在驚聲廣場看日落,「光是圖書館坐個透明電梯就看到海。」反而比較少動筆。刪除手機裡的社群軟體,她開始參加水上救生社,爬山、游泳、騎車玩北海岸、夜遊。回想起來,這一年反而沒有太多的作品。「愈不快樂的時候愈有東西可以寫」,她笑著露出虎牙和小梨渦,單純的像個小孩,令人難以和她成熟的文筆聯想在一塊兒。
這學期張嘉恬成功申請至巴拉圭實習,唸西語系看似與她的創作之路沒有交集,但對於感情細膩的她,誰說不是展開了一扇跨語言的創作之窗?

第39屆五虎崗文學獎散文組首獎張嘉恬。(攝影/吳沂諠)
#### 【第39屆五虎崗文學獎散文首獎作品】嗜甜/西語三 張嘉恬
清明時節,天是灰的,雨是細的,連續做了兩天夢的大腦,想起了今天是祭祖的日子。
三十五過後變得很不長記憶,比母親那時足足早了十年。幸虧工作上的事還記得來。也是,混了十幾年的圈子怎麼叫記憶不長好?但其餘的,似乎也就是隨著節日,被動地倒數一年的消長了。
和姨約好了上市場,捎去一通電話,我們在四海豆漿合吃一套燒餅油條後才動身。
四月的早晨清冷,上星期起外出就都得帶著傘,唯一一件米褐色長背心就這樣陪著自己在辦公室和家裡奔走。
奔,那樣歡快的字眼,不知為何,總使我想起馬蹄聲。最後兩筆畫恰似馬兒踢踏的雙腿。馬鞍的鬃毛上汗滴粼粼。馬兒在無止盡的荒野狂奔。
「買個豆皮。」姨說。
「哪種的?」
「煙燻。」
「煙燻的好,我也愛。」多拿一盒,晚上找姨來下酒菜。
市場人多,儘管已到了歐巴桑的年紀,始終學不會阿莎力地喊價。在這種時刻,做一個優雅的歐巴桑竟也有些格格不入。
總歸是太少出門買菜了。
工作總是不知不覺拖到晚餐後,吃習慣了夜色配飯,連開伙煎顆荷包蛋都像什麼大費周章的事,住家樓下的便利商店,於是成了陪我趕企劃的好朋友。
姨不是。從來都不是。
只要有雞湯喝的日子,都是姨拿來的。她用她那小提鍋,煲剛剛好兩餐份量的湯,若是我不在家,她便寄放在警衛室。
香菇雞、麻油雞、大蒜雞、九尾雞、烏骨⋯⋯什麼東西現在都貴了,我不准她亂買,當然她也同樣看不起便利商店裡的冷凍雞湯包。
今日的廚房又要歸她,一路忙到十點,總共五菜一湯。姨講究,雖然嘴巴裡說簡單弄弄就好,但我媽愛吃的那幾樣都沒少,又是涼拌又是過炒,倒是我就像廚房裡多出來的那一個。
正想著,姨往菜籃裡丟了一大把空心菜、一根苦瓜⋯⋯天啊,苦瓜,我得叫她自個兒帶回去吃。一片冬瓜被拿起又放下又翻面又近看了半晌,同樣在一旁香菇堆東翻西找的歐巴桑勸她就拿起來吧,都是人家菜販一早就去新鮮現批的。
結帳時一共是三百五十五,幾年來這個時節的菜價並無太大改變,薪水也是。
錢會薄。父親可能還是那句話。但該花就花,然後大氣地追加一大朵白花椰,儘管花裡的小蟲兒都不是他在挑。
我呢,既然連煎荷包蛋都懶了,也有些時日不曾挑過花椰菜。
母親過去拜外婆大抵也是這樣,炒茄子、四季豆拌木耳、蘿蔔炒蛋、幾樣水果,十分家常。
去程時在路上買杯拿鐵,因為外婆嗜甜,必須點嚇死人的半糖。
回程時那附近有個張家燒餅饅頭,他們總會買一袋,吃不完就冰起來,好幾個早上都可以蒸來烤來吃。
「呀!這鴨腿燒的多漂亮!也適合下酒哪!」姨不知何時,已經晃到熟食那排。在這裡買的,十個有九個最後都進我家,畢竟姨一個人,也吃不了多少。
我則跑到市場裡生意最旺的春捲小販那,看他們 俐落地包餡、束口、找零。這間春捲店從我有記憶以來,排隊就排得嚇嚇叫,還登上外媒報導過。過去利索地包著餡料的老面孔,如今都變成穿著時尚的年輕人,客人來來去去,桌上那盒花生粉倒讓我想起什麼。
「老闆娘,三捲。一捲糖多點,兩捲不要糖。」春捲似乎和拿鐵不太配,但清明時節,總是應景。
母親這些年來也喝了不少半糖拿鐵了吧?和素菜也是怪異的組合。
我也嗜甜,或許是母族那邊的遺傳,只是晚年覺得母親真的喝太甜了。
「你這刀該磨磨了。」
「反正也不常用。」我洗去空心菜梗上的碎泥,漫不經心地回答。
「丫頭你喲!」
丫頭,父親和姨是唯二會喊我丫頭的人。每次被這麼一喊,都感覺自己變得好小好小,小到拳頭還像一顆石頭大小,被另一個掌心包覆,牽著我走過擁擠的夜市。
被喚作多久的丫頭,就被護在掌心多久。
我的確該找個願意收著我的傢伙了。管他高矮胖瘦,大齡未嫁本來就像老人斑,只會讓自己在人群中顯得突出。
真可怕,父親那會兒總是說,等我一嫁,就把家裡的鎖也換了、鞭炮放下去,讓全社區的人知道。結果現在倒好了,我那把家用鑰匙上還有他送我的機車鑰匙,十八以後就這樣子圈在一起直到三十八。
「丫頭,你想什麼?煮水拌味噌呢!」
我應了聲好,每到這種時刻,任何讓我在廚房有一點參與感的事,我都樂意做。褐色味噌像岸邊的細沙,自碗壁逐漸流失,和進碗底的旋渦
姨一直都很好命,六姊妹裡頭數她嫁得最好。貸款什麼都不必她來,一輩子沒工作過,成天只需煩惱家裡清潔,於是便像隻勤快的馬兒,在菜瓜布和馬桶刷間來回、在曬衣架和流理臺間奔走,家中各個角落都乾淨溜溜。
她還有大把大把的時間看做菜頻道。打掃、上菜市場、煮飯,小摩托車十分熟捻地鑽著人擠人的市場。
那時候,姨和母親也是這樣。她們兩個女人肩並肩坐著,餐桌上有個鍋子,一鍋挑好的菜、一鍋菜根、一鍋母親挑完姨又挑了一遍的菜。我在客廳吃零食,一會兒就聽見嘩啦啦的水聲和抽油煙機轟轟轟的惱人聲音。接著一盤盤油亮亮的菜一一被端上桌。
我想起老師說過,拜拜完的食物都會少一個味道,因為靈魂真的來過。
但我記得那些被供在佛祖跟前的菜依舊下飯,也依舊是我熟悉的母親和姨的手藝,偶爾瞥見一點紅灰紅灰的碎片,大概是外婆在尋找哪一盤是自家兒女帶來的菜時,不慎抖落的香灰。
而輪到我們這些「活人」進食時,外婆就在牆上相框裡看著,好在我們幾乎都把食物通通塞進肚子裡。
我經常想,如果哪一年,換我替姨做飯,該準備些什麼?
姨那麼挑,腸胃又不好,要是沒吃飽怎麼辦?不會托夢指定非哪個市場買的菜不可吧?
會不會三炷香都燒完了,菜被灑了一地,姨不領情?
想到這便覺得好笑,這一笑不得了,眼淚都逼出來了。
車子行駛中,雨又下下來。姨倚著窗小憩。每踩剎車,那幾葉陶瓷小碟就挨著彼此打顫,彷彿初春的寒意也淅瀝瀝滲進保鮮膜來。
姨睡著了,我喚了她也沒醒。看來這次又不下車了。我只好代她點上她的那一分,並將茂谷柑、蘋果排排好,雙手合十。
「明年開始不給你們喝那麼甜了,太不健康了吧!這個味噌我有幫忙做喔,畢竟自己住,還是會煮一點的。姨最近手又在抖,說是自律神經失調,味覺有時後也失靈。如果覺得菜偏鹹,多喝水不然就配拿鐵蛤!」
然而我環顧供桌上各式各樣的餐食,有孔雀餅乾、鳳眼糕、乖乖⋯⋯,都是小時候的零食。難道離開這世界的人們,都會懷念香精和過多精製糖類的味道嗎?
母親以前總是愛吃摻了焦糖的古早味布丁,冷凍裡也總會囤幾隻綠豆沙冰棒,年輕人愛的甜食,大抵上她都能接受,吃得比我還兇,但現在就不能再縱容她了。那會兒她是被什麼什麼癌搞垮的,我不希望她轉世投胎還自帶糖分。
所以說到底,姨或許還是對的。吃得挑惕,活到呷百二。
再一抬頭,觀世音斂目低垂,大殿和我這兩日的夢有幾分相似。
第一炷香開始冒煙,我想起了夢的內容。
那天是清明時節,天是灰的,雨是細的。夢裡的孩子掉了牙。夢裡的孩子痛醒了。
夢裡的孩子吞了桌上的一把糖,夢裡的孩子睡著了。
#### 〈嗜恬〉評審摘錄
*對話纖維化的應用非常有小說感,更容易挑動讀者進入情節,是較獨特的做法。場景好看,大量使用食物的書寫引人垂涎,並從中探討人際情感,引發思念之幽情,各式情感細節都藏在細碎的語調之中,是成熟到不得了的程度。(王聰威)
* 對話本身就是聲音,推動情節發展,可以彰顯說話人物的個性。整體的內容和形式等方向都不錯。但「你、我、他」和「人、神、鬼」之間卻無法找到相關的對應。 (李瑞騰)
*能夠把自己的工作、家庭、生活俐落地交代出來,是教科書等級的示範。對「姨」個性和習慣的描述很細膩,並用「嗜甜」作為家族情感的串連,傳達了對逝去家人的思念。結尾也很不錯,「孩子」一詞究竟是指自己還是媽媽呢?厲害的作品就像如此,最後皆讓人有不同的解讀。(沈信宏)
#### 【第39屆五虎崗文學獎小說組首獎專訪】
#### 林祐任善用小說意象 探世界幽微變化
【記者蔡怡惠專訪】「某天凌晨有感而發,」林祐任談起〈懸掛〉的創作靈感與寫作動機表示,它與自己生命中的經歷毫無重疊痕跡。他說,身為一個人、一個創作者,生活往往有諸多想抒發但缺乏動力下筆的事情,「但《懸掛》出來的那刻,就覺得非寫不可。」
「《懸掛》問了這個社會一些問題,同時也展現出獨特的對於日常生活上的聯想與行徑方式」不論是在語言還是詞組順序上,林祐任都不斷嘗試跳脫常人的書寫框架及邏輯,試圖詮釋一個全新又衝突的故事。於他而言,《懸掛》並非一篇愛情故事,林祐任想問社會的,是一個家庭對於一個個體可以造成多大的影響,是扣問主角之間的權力結構。
「不去試著合理化所有的暴力其實都擁有一種迷濛的美,於是矜持、保守、玩笑,不離開既定界線,轉而對火畏懼、崇賢深海,卻離不開身陷的泥淖。」林祐任解釋,這即是為何小說裡的角色,在某種程度上看起來骯髒的原因——一個朝著死亡奔去的少年,不斷透過違背常理的矛盾行為,娓娓道出背後令人力不從心的現實困境。
小說形式多種多樣,每個人各有不同的解讀,林祐任則將其簡潔扼要地定義為兩種形式,其一為給讀者勇敢接受的機會,其二為喚醒眾人的危機意識。「我希望讀者們能從《懸掛》看到這個世界幽微的變化,找到屬於自己的歸屬感。」提及平時如何精進自己的創作能力,他感謝「思考訓練與溝通藝術」這堂課的老師黃文倩,多虧她推薦的大量文本,以及課堂上邀請的講師張潔平鼓勵他們「平時多看、多去路上走,趁你的筆還鋒利時盡情的寫!」讓他學會用細膩的雙眼去觀察世界靈光繽紛的一面,不管寫的好壞於否,都盡可能的保留寫作的習慣,讓練筆成為一種例行公事,久而久之便成自然。寫作路上,林祐任分別列舉文壇作家邱妙津、郝譽翔、雪維雅.普拉絲(Syliva Plath)、韓麗珠,透過他們對於文字的頗析,讓他或多或少在處理《懸掛》一文上,獲得不同的啟發,也改變了他各個人生階段的書寫文風。
鍥而不捨寫下去的意義在哪裡?林祐任引用作家李昂在其著作《年華》一句:「書寫為的是在我的創作過程中留下記憶。」很多時候創作除了紀錄自身在大時代下的痕跡,更多時候是想要書寫那個時代的興衰與哀愁,把文字倒進時代洪流裡,開拓出屬於自己的一片文學淨土。《懸掛》文中最令人驚艷的彩蛋,即是林祐任對「皮帶」意象的描寫隱喻,皮帶橫拉時代表著主角穿越隧道時的癲狂;直拉時象徵主角對於父親施暴的恐懼;隨意放置時的彎曲垂墜,則表示蜿蜒綿長但發臭腐酸的腸胃道。關於主題核心,皮帶的「懸掛」、頭顱的「懸掛」,都持續的緊扣小說標題,暗示死亡的前奏細膩且餘韻猶存。
談及淡江與自身創作的關聯,林祐任指出淡江大學的文學思潮走在時代前端,是他見過最不保守的,自己從朱天文的《淡江記》 裡看到很多的異想,更從中發掘出知識份子的另一個面貌。他說:「淡江大學對於人文的影響或許還沒有在我身上明顯現形,但在其他優秀的作家校友身上卻已經昭然若揭。」
#### 【第39屆五虎崗文學獎小說組首獎作品】懸掛/德文二 林𧙗任
他睜開眼睛的所做第一件事情,是順著驚恐往下觸摸,觸覺的存在是為了證明
——今天怎麼仍又活下來了。這是我很久以後才知道的事情。
求證是環顧四周想要察覺夢的身影,或是任何不屬於這個地球的生物,以此作為自己是否已經死亡的依據。在拿捏好觸覺與嗅覺,嗅出鬧鐘的無理取鬧後,就下地,讓失望蔓延在關於昨天的禱告失效,上帝的拒絕接聽。
於是,他的一天就被迫展開了。
他首先是物色一次性的洗臉巾,犧牲其生命以成全自己的乾淨與整潔。他享受抽取紙巾時,彷彿拉開拉鍊「滋~」的聲音,如上揚的笑聲一般,將他帶到自己無法製造出來的快樂之中,或者是他從未感覺到的那些,與知足非常相像的東西。
接著是沖涼,把睡意趕入冰冷的地下水道,使瞌睡的影子柔軟滑入一般人無法想樣的廢水處理場,也可能,無邊無際的大海之類。
他們說,房間代表的是一個人的內在、靈魂。我們的房間如他一般,在看似溫馴的外表背後,是藏在內裡的十分紊亂。地上是讀書留下來的橡皮擦屑,浴室裡是毛髮;鏡子上則是牙膏泡沫;桌上堆疊著書,沒有一本被翻閱或看完。
他說,沒有時間打掃的原因,是因為忙碌於課業與睡眠的平衡之中,基本上,他每天幾乎都只睡不到五個小時。這可是我親眼目睹的。有時候是因為功課,但更多的時候,源自於睡魔的召喚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再加上焦慮與不安使然,他需要靠著比較激動的方式向異世界表達自己的不滿,因此當晨光靜靜地撥開房間的窗簾時,他只是納悶昨天晚上,到底有沒有清楚地跟夜晚的魔鬼與精靈好好地表達自己的訴求。
「你知道一天睡眠不足,卻又要上課的感覺是什麼嗎?是外容姣脆如花,內裡翻騰痛苦如海浪。泡沫如具象化般地襲來,讓你以為你要與他們同類。」
「你什麼都不懂,卻要我在勞累的時候冷靜?」
「到底要怎麼冷靜呢?你有想過嗎?當體內的空虛感過於膨脹時,我就需要不停地說話。彷彿喉嚨的閘門破了一個洞,肺部空氣鮮活,不說就得耽溺死於裡頭,於是我只能一直說、一直說,說到自己說錯話為止,再祈求他人原諒。」
「但又有誰會願意原諒一個,身懷他人無法理解之病的人呢。就連我都不願意原諒自己了。」
反覆的說詞,得在我的身旁一直說、一直說,說到他累了,方肯在我的床上入睡、罷休。
每每如此,都讓我恍若有種自己是睡魔的錯覺。
他經常夢見他的父親。強壯且不可忤逆的神聖樣貌。
在他的世界裡,父親就是神。不可褻瀆。
他害怕他的父親。尤其是他的皮帶。
他的父親我見過幾次,也說上幾回話。雖然我也無從分辨什麼才是「破碎的價值觀」,但他的父親似乎也沒有像他說的那麼離譜。
在他的眼裡,父親擁有一副吃人的獠牙,將他的夢咬碎;過於炯炯有神的眼瞳,一眼就看出他的失敗;寬大的手掌,不是將他的童年有力地撐於自己的肩膀之上,而是幾個響亮的巴掌,瘮人地烙印在他生活裡的每一個角落。
當他彌留於沉倫與清醒灰色地帶時,他總能聽見幾個突兀的撞擊聲於耳邊環繞,彷彿他從很早以前就冀待卻又不可得的稀落掌聲;又彷彿是赤裸的威脅,正在壓抑他過於飽滿的自尊心。於是在他呼吸的每一刻,他都能毫無餘力的保持清醒。
我曾藉故到他的家裡吃過晚飯。因此也順道見了他的家人。與父親不同,他的母親是位既擁有智慧,又保有自我的女人。在基金會擔任無償志工、記者,和參與社團的同時,卻又兼顧得了家庭,尤其燒得一手好菜。
甜不辣與韭菜,一盤盤盡是橙紅柳綠,聞著溫和之外,嚐起來也並沒有惱人的膩味;綴在紅燒獅子頭旁的,是一片片白菜,透明,好比如幾朵蓮花花瓣,在混濁的池水中載浮載沉,獨顯高雅、入味、並且不留於爛。我頓時興致高昂,嚷著要與他的母親學藝,最後竟開始討論起要如何控制火侯,才能端出熟嫩不老,也不沾毛豆清香的雞肉丁塊。我們甚至聊保養,因爲他的母親就算早已年過半百,卻神奇地從未擁有一定年紀者的自傲與庸俗;相反地,像是從古書裡走出來的人物一般──她不自覺地顯露出一股異於現代人的緩慢、智慧、與雅態。
「我沒有什麼在保養耶。」他的母親說,自己頂多偶爾染個頭髮,若否,那便是白絲垂肩,偶爾看著,竟會有股滄桑與煩躁。我相信她,畢竟她的書桌僅擺滿眾多出版社的叢書。看不見保養品半罐。
他的父親在成功男性的話題上十分健談,從運動到金融海嘯,再從海嘯聊到女人。
我看著他說話的神情,看見男人那種低俗的幽默與自尊在此顯露,獸性流於媚俗。比起這種讓人感到絕望且厭惡的主題,我比較想要探討的是台灣一直保有爭議的學測與指考,還有學生由高而下的短暫人生。
我懷疑這一切之所以會發生,還有在話題上的低級選擇,都只因為我是個男性。
大家總是喜歡幫我預設立場。
當他的父親在與我談話的過程中,我看見他的父親熟練地將皮帶解下。
他的眼神斜睨了過來,夾雜著鄙視與痛苦的神情,在臉下成形、混合,做後竟有些不成人樣。我不忍直視,硬是將頭扭了過來。
皮帶被安置在沙發的靠背上,像一條繩子隨時要蠢蠢欲動的幻象。他的父親有些不好意思地解釋說,這一直都是自己的習慣,這麼做是為了讓剛吃過的東西比較容易穿越腸胃道,進入消化系統。關於這句話,我的思緒被帶到他曾經在夜晚時帶我到山上俯瞰整個台北市。
那晚,我在浴室內聽見他放下包包,又隨即拉開拉鍊的聲響,我以為是自己聽錯了,有關他居然會在凌晨兩點煮熱開水的聲音。
當我拉開浴室的門時,我看見他興致沖沖地站在門口。手裡拿著兩頂安全帽。
他說:「我們現在上山。」
『現在?』我全身只圍著一條浴巾,冬夜的冷冽啃咬著我想要將衣服穿上的心智,我甚至分不清,我到底是因為冷,還是因為被他瘋狂的提議給嚇個正著,於是我萬分錯愕地看著他。
「對,現在。」
我們穿過長長的隧道,他騎得飛快,我被他突然其來的瘋狂給唬得也有些放縱,想要趁機放開緊抱著他的雙手,去感受強風勾過手指的快感,但隨即我立刻被理智快速的扯回來。我知道當其中一人徹底瘋狂時,另一人至少得清楚自己在做什麼。
不造成他人負擔,是我給自己最大的自我期許。但很顯然不是他的。
我們主修不一樣,什麼都不一樣,只有學校一樣。
他驕矜、放縱、瀟灑且俊俏,他不知道,他從不滿意的自己,是我最渴望成為的樣子。
那晚,我們無視明天的課程,思緒與眼裡僅被銀光閃閃的台北市充滿。台北,彷彿一滴一滴的眼淚聚成寶,形成金光閃閃的聚寶盆。明日的太陽與未來,睡眠與妖精,都露出了訕訕的微笑,旋即離開了我們的頭腦。
「你覺得呢?」
『什麼意思?』
「這一切啊,不然還能有什麼?難道⋯⋯」
知道他要用可怖的故事嚇唬人,我趕緊緊他嘴巴裡滿滿的笑意。
照理說,我理當要好好地抓緊機會與他一起讚嘆北部地區的繁華、瑰麗、以及誘惑。大談我們的夢想。像是努力拿到獎學金,研究所,畢業後到結婚(一如他一直想要的那樣)。但不怎地,我卻一直想起我們穿越的那條,長長的、彷彿沒有盡頭一般隧道。
那條隧道直到現在,仍然在我的頭腦裡懸掛著。我恍若再次回到那個地方,站在一條發臭、到處瀰漫著各式酸味的腸胃道,因為無法饜足,所以竭盡所能地去消化掉世界上所有好吃的食物,再交給身體去排泄。
難道,這就是為什麼所有所謂「成功的人」都是瘋子嗎?他們想得太多,庸人自擾。意象盤旋,無時無刻都在虎視眈眈地想把我們吞嚥而下,直至世界的最底。
其實,通過世界的腸胃道還不是最煩的,最羞辱人的事情,莫非是當你於底部呼救時,知道自己此時的處境,堪比垃圾,待處理,而且終將被忘記。
這是人生於他眼裡所呈現的樣子嗎?
我忽然可以與他一起看透他所有的渴望,以及深深的絕望。
皮帶的用途有兩種,一種是拿來抽人,另一種是使頭顱懸掛。他說,他的父親是前者,而他天天冀望著後者的來到。
我們經常為了很小的事情吵得不可開交。
我不肯跟他做愛,是其中一個原因。
我說,性別錯誤的太離譜,做愛是完全不可能的事。你要想想當初我願意和你在一起,是因為你曾經答應我,你將發誓讓我捍衛自己的生存界線,或者是掌控自己身體的權利。我仰慕你,因此和你在一起。你是我強大而不可忤逆的巨神像。對我來說我們的關係可以很乾淨。可你偏偏要往髒的方向發展。
「我不要喉結,或者是任何能夠滋養我體內那株蘋果的東西。」我往往會用極其肅穆的語氣這麼下出定論。
而他憤怒的時候好似他開心的模樣,行為舉止也異常雷同。他向我的身上砸水壺、鉛筆、或者是將咖啡潑向我。使我病懨、青藍、過於瘦弱的的身上浮現海島,更多的藍。過程像是板塊移動,一塊大陸剛沉至海底,另一塊緊接著浮上來。我們非常地刺激,有關這段關係,接著,我們歡快的愛,但我從來只感覺到激情與亢奮,任何跟愛相關的事物,都沒有在我們的碰撞中被激發出來。
當我順勢在他的身上刮出指甲的紋路以當作報酬時,他總是能用更野蠻的方式將它們通通推還給我。
這種事情對我來說只有當下值得一試,就像將手鬆開這件事,很瘋狂,但也很麻煩,因為我還得花上半個鐘頭進行事後的清理。但責任不在於我,怎麼會是變成我要去解決爛攤子呢?
但使我更厭倦的是,在一方面,我得多留一份心神去觀察身上的世界局變,而又得在另一方面去搪塞他人──為何我總是在夏天套上厚重的長袖與大衣。
「皮帶的用途擁有兩種。」但不論是前後兩者,我似乎都已經深之入骨地感受到了。一如當他硬性製造謀殺氣氛時,我憤恨到進入想要奪走一切的瘋狂;當他熟練地壓制我、將手臂挽著我的腿部時,我所感受到的男生那種生而可悲的視覺上的刺激;而當他的手掌狠狠地掐住我的脖子時,我曾錯以為,我是他失去已久的父親。
我的傷口繁茂昌盛,安然待揭。
天氣在下午猝不及防的熱了起來。「會中暑。」在老師的要脅之下,我不得不脫下厚重的衣物,讓無數隻眼睛飽覽我身上的世界地圖。他們指指點點,彷彿我的身體上,真的長了一個佛羅里達或是加州。
「你這是怎麼回事?!」C問。
『你說呢?』我略帶嘲諷的這麼回答她。但就算是表面一副冷酷的表情,我仍然不清楚自己本意是在急於吹熄心中那塊搖曳不定的燭火,還是想要以冷酷的招式,嘗試阻擋他人無用的高談闊論。
「你的家人知道嗎?」
『他們不必知道這些。』我撒了一點謊,『我父母親對我做的,也許不亞於這些。』但至少這對他而言,是真實的。
「你這樣很不健康耶。」C看起來被惱住了,彷彿我身上的暗沉將會因為談話,緩緩轉移至她的身上一般。我感覺到一種看似溫柔,卻飽含著疏離的援助,「需要幫你報警嗎?」
『哈哈哈,不用。況且,我從來就不希望有任何人覺得我是聖潔的。』
我心裡太清楚世界的運行規則了。聖潔,只是我們從小至大被教導需要成為的一種意象。他們引領狼群入室,於是我們跟進,進入一個薄膜背後,即是骯髒的可怖世界。
不去試著合理化所有的暴力其實都擁有一種迷濛的美,於是矜持、保守、玩笑,不離開既定界線,轉而對火畏懼、崇賢深海,卻離不開身陷的泥淖。
講到這裡,我只是想要對你說:你對我而言,不只是一種由下而上的撫摸而已,如果這是沉倫的話,那麼,我們所擁有且經歷的一切,都只是在證明──我很正常,而且為了你,我正在朝聖潔的反方,義無反顧的跑去。
但事發的隔天早晨,我們依然躺在一起,而他懶洋似一隻忠誠的大狗,於我的床上、我的膝上、我的心上,再度跟我叨念睡魔與精靈的不眷顧,以及祂們是如何偏袒我。靠著我的心臟,蜷縮在我的懷裡,不告訴我他有多愛我會有多抱歉,或者可能後悔他沒有再下手更重一點。
我如一個慈母,用手指玩弄他褐色的髮絲。我想要他的髮色,一個屬於有外地來的人,那種由內而外的思維邏輯大不相同,但或許我更渴望的,是一種新的身分跟顏色。
不論是情慾也好,顏色也好,每次當這種事情發生時,我絕對不會忘記,但或許令人詫異的是──我居然沒有任何一點想要離開的念頭。
我認為發生的(或已經發生的這一切),僅僅是因為他在這段關係中,獲得不了他要的幸福而已。獲得不了自己想要的那種瘋狂,我似乎能夠理解一點。
一如他與他父親之間的互相要求,互不理解。用兩縷悲哀的眼睛底點燃戰場裡的各自立場,解決方式僅有征服。也或許,別有他法。
近幾天,他的狂躁已經明顯到有些藏不住的程度。原本保有輪廓的眼睛往外邊出逃,強健的身體明顯像失去嚐鮮期的百香果一樣,突然地乾癟、消瘦,就連在打我時,(我很抱歉得要這麼說),都讓我誤以為是誰在搔癢,但回過頭時,我卻看見他憤恨眼神裡的那種空洞,沒有初衷的雙手彷彿沒有初衷的性器。他也不跟我歡愛,睡覺成為了他新的生活重心。
他的腦袋彷彿沒有任何東西,而眼睛下面僅僅是樹根,撐起他綿軟的腦袋與兩顆眼珠。但不論如何,看得我心驚膽跳,彷彿那是我,或者是我的腦袋破了一個洞。
「我以為我要失去他了」的念頭,從一個月的偶爾想起,到近幾天如雨後春筍般地冒出。到最後,我根本不理解我到底是因為擔心他,還是期待這一切可以趕快發生。讓我成為在場的人,趕上歷史必然的詭局與變化。
他有那麼幾次苦笑著看著我,不再逼我與他歡愛的時候,惹得我心生猜疑。
我不瞞任何人,我仍會害怕,畢竟我們的性行為並非安全。於是我穿著短袖,大膽地去醫院掛號。我聽見自己說,我要做愛滋病的相關檢測。三十分鐘後他們致電給我,說要約個時間談。
「我沒時間。」我在學校裡的某個角落這樣回覆他。原本我在七樓自習,但因為圖書館內無法說電話,因此我大老遠跑到廁所,卻又因為訊號太差,只得到一樓接電話。雖然是我要求了這場體檢,但我的耐心已經完全耗盡。我只是想要知道一個答案而已。
我看見我們之間那長久的空白期,我模仿著他的口氣,向電話的另一頭說道:「不論結果為何,我都比任何人還會沒有時間。」
電話那頭傳出細微的呻吟聲,緊接著是密集的窸窣聲,好似某種不能被我知道的密談。一段時間過後,自稱是負責我病情發展的醫生的人獲得了話語的主控權。他首先是感謝我願意來體檢,再說出一些無關痛癢的話。最後,他才終於道出重點:「恭喜你,結果呈現陰性。」
我連謝謝也不說,就把電話給掛掉了。
既然不是愛滋病。那我也不知道是什麼了。
反覆異常的,原本能夠獨立思考的,卻又過於亢奮以至於無法掌控自己的。那樣的一種人。
雨下得很大,心情低落,不澎湃。因為有個重要的報告,我五點就起床了,灌了三杯咖啡,卻仍然覺得心情上少什麼。通常在喝完咖啡以後,我會跟他一樣亢奮,說出源源不絕的話語,而且通常不是什麼好話,彷彿體內有座高污染的河流,我大概無法給予他人開心與幸福。給予他人工業區般的痛苦,是他教會我的事情。然而,這幾天,他異常的安靜,也不笑,臉上呈現的僅僅是一種虛構的空虛,彷彿某種小說走投無路時,會出現的那種虛空場景。
我沒有想過這樣的畫面會出現在他身上,也沒有想過我會這樣形容他,讓我之前覺得的所有不可能,在我們之間一一應驗。
出自於這個原因,我忽然想到他,他的臉與他的父親,還有他的母親。三個看似進而遠的血緣關係互相堆疊、離開、重組。最後這三張臉通通撲向我,彷彿我是一隻需要被捕獵的任何一種東西,最後穿越我的身體,與我融合。我看著眼前的景象,可怕地認為自己勢必要回家一趟。
「我熟悉電梯、天花板和自己的距離。因為他們都跟死亡有關。」他曾經在快要睡著之前,用一副囁嚅卻又不能不說的方式,將這句話給吐了出來,灑進我的夢裡,到處都是,或者是其它。很不負責任,就像我們曾經歡愛的那樣。不負責任,他非常擅長,而我深深懷疑這有沒有讓他好多一點,或是比較快樂。
因為當我看見他的頭顱懸掛於天花板上,以自己的軀幹去作為上空與地下的分界線時。我知道,有一股像是瘟疫之類的東西,正悄悄地與他的身軀剝離、爬出,攀附於我,並且,永不分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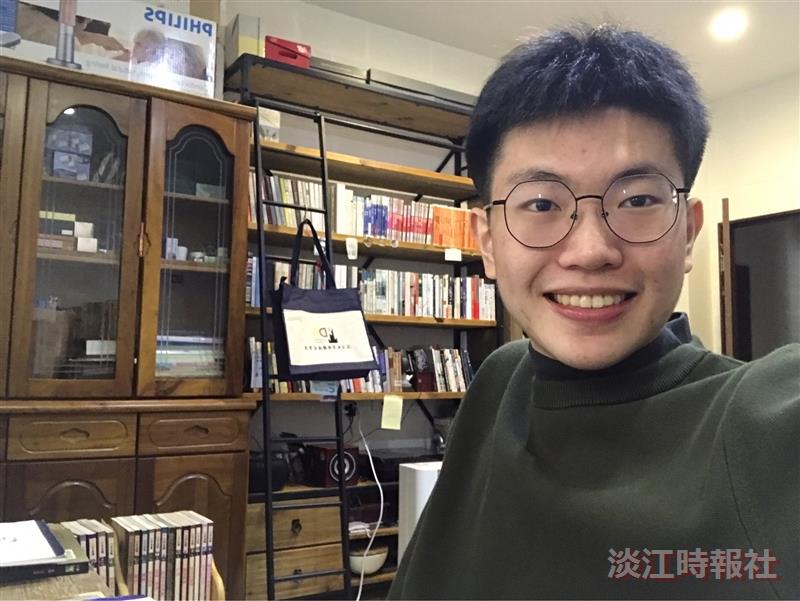
第39屆五虎崗文學獎小說組首獎林祐任。(圖/林祐任提供)
#### 《懸掛》評審摘錄
作品《懸掛》呈現出的整體意象、劇情的收斂及外放、「皮帶」代表的多重象徵,和對於性及愛的細節詮釋都十分完美,將感情的剖析體現的淋灕盡致,是絕對有能力打開文學拜占庭大門的創作人才。(陳栢青)
這篇作品讓我想起卡夫卡寫給父親的信,在比較難體悟的情感描寫上處理的很好。(鍾文音)
我認為作者林祐任為高手,在小說內容的敘事、埋下的路徑都相當自覺。《懸掛》的疼痛感及複雜性,造就其獲獎的原因。(張亦絢)
關鍵字
#五虎崗文學獎
#首獎
#林于勝
#張嘉恬
#林祐任
本報導連結
#SDG4優質教育
NO.1170 A
| 更新時間:2023-10-03
| 點閱:562
| 下載: